您现在的位置是:生活百科网 > 生活百科 >
纹绣培训优等质兰(兰州纹绣培训)
2022-05-05 14:27生活百科 人已围观
简介楔子清晨喜鹊登高枝欢畅啼鸣,前缘坊里人声鼎沸。佟家夫人焦氏亲临,来坊里取一幅由坊主兰鸢亲制的双面观音绣像。据说,佟家老夫人卧病在床多日,焦氏急得夜不能寐,亲自求上...
楔子
清晨喜鹊登高枝欢畅啼鸣,前缘坊里人声鼎沸。佟家夫人焦氏亲临,来坊里取一幅由坊主兰鸢亲制的双面观音绣像。
据说,佟家老夫人卧病在床多日,焦氏急得夜不能寐,亲自求上香火鼎盛的静音寺,历经千辛万苦终得寺内一高人的指点,即,为求佟老夫人痊愈,必得于家中供奉一幅观音大士的绣像。
那高人还言,绣像需得悬于静室中央呈南北向,万不可厚此薄彼了任一方。如斯以来,普通绣像自难入眼,也唯有双面绣像可示虔诚之意。
彼时坊中人潮涌动,亦有好些与佟家颇有往来的妇人们,或真情或假意地慰问一番佟老夫人的身子。
她双手合十放在胸前,叹道:“银钱乃身外之物,我如今就盼着这绣像真能如高人所言,早日换得婆母的身体康泰。”说罢,似有些气力不济,连脚步都虚浮了起来。
“夫人,您这几日不吃不喝地服侍在老夫人身侧,整宿整宿地都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”
前来相扶的丫鬟忧心忡忡,有心压低嗓音,却因天生就不是个轻言慢语的主,反叫周遭人都将她的话听了个清楚。
“别的也就罢了,您还在佛前潜心跪了足足七七四十九个时辰,便是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的呀。”
“莺儿,说这些做什么。我既为人媳妇,自是要尽心侍奉翁姑,方不负为媳为妇之本,”焦氏低声轻斥,又羞赧地向众人行了一礼道,“是丫鬟不懂事,叫众人见笑了。”
“不会,不会。”众人纷纷摆手,“有这般孝顺的儿媳尽心至此,佟老夫人真真是好福气……”
二人在雅室重新落座,四目相对时,彼此的眼底都是心照不宣的揶揄。楼下窃窃私语未停,焦氏如听笑话般,将窗户悄悄推开一条缝。
“就佟老夫人那难缠的老货色,能得了这般孝顺的儿媳,真真是前世烧了高香吧。”
“谁知她是真心还是假意,当初佟老夫人在外头也说得有鼻子有眼,一字一句皆说她的儿媳不孝,可结果呢,等到那焦家人闹上门来,才知其图有虚词。”
“……”
焦氏听了一耳朵,便觉索然无味,干脆合上窗户,拿着身前的茶水轻啜,而后满足地喟叹一声。
“佟老夫人不惜将自己折腾病了,也一意要磋磨于你。你如今这般行事,虽说能在外头树立个好名声,可这没日没夜地紧绷着神经,到底于身体无益。”
兰鸢为她续水,见她眼下青黑,不由得面露忧色。她自是知晓佟老夫人磋磨媳妇的手段的,也正是因为知晓,才为焦氏的不以为然而担心。
“我早就不是当初的吴下阿蒙了。”焦氏“噗嗤”一笑,心底暖流涌动。
她伸出手拍了拍兰鸢的手背,俏皮地眨了眨眼,探过头来悄声说道:“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哦,我那好婆母的病,才不是被折腾出来的。”
1
佟家长子佟冶外放三年,于吏部考核中得了个优等,遂被委派回家乡任通州府经历。其妻焦氏携子先行回乡,于府中打理一应事宜。
彼时,府中由佟老夫人马氏当家。马氏见儿媳归来,一双老眼中早就精光暗闪,当天晚上要求焦氏为其值夜。
焦氏柔顺应下,一如当年般怯懦低眉,老老实实地卷了方薄薄的被子,睡在马氏的脚踏之上。
夜间,马氏起夜频繁,又总能寻些上不得台面的借口叫焦氏端茶递水,每每折腾至下半夜才肯勉强睡去。
待至第二日清晨,她又叫焦氏随侍身旁伺候洗漱,不肯放其离去,短短几日便磋磨得焦氏面容憔悴、神魂难休。
马氏心中畅快,虽说自己也被带累得没睡过一日好觉,但想着又重新将儿媳给拿捏住,瞬间便觉得那一身的腰酸背痛也算不得什么。
当初焦氏一进门便被她囿在身边,每日里立足了规矩,端茶递水、请安值夜,焦氏无一不从。若她生了厌烦之心,也是能张口骂得、伸手打得。
她自是以为焦氏不过一温顺的兔子,是以更生了几分轻慢之心。
哪知会咬人的狗不叫,焦氏这贱妇竟在暗地里使了手段,诳得全家都允了其跟着自己的儿子去了外放之地,可惜她的一番筹谋都没了用武之地。
还好,不过脱离掌控三载,如今定还要其重新忆起自己的厉害。
她如是想着,就连在梦中都不自觉扯了扯刻薄的嘴角。她只以为蜷缩在脚踏上的焦氏只有在梦中暗自垂泪的份儿,殊不知于寂寞夜色里,焦氏早已悄无声息地爬起了身,静默地立在她的身侧。
焦氏见马氏已然睡熟,淡漠地从茶炉上汲一碗微温的茶水倒进夜壶中,而后悄然掀开马氏的锦被,将夜壶里的遗尿缓缓倒在她的身下。
马氏本就自我折腾了大半夜,此刻虽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自己身下有几分难受,可到底难以睁开困意重重的眼皮,只得无意识地嘤咛了一声,又侧过身沉沉睡去。
湿热的尿液点点晕染,慢慢泅进马氏身下的锦被中,形成不大不小的一片印记。
焦氏嘲讽地勾唇一笑,待放回尿壶后,重汲一碗茶水在手,又狠狠掼向地面。
“啪!”清脆的瓷器碎裂之声划破夜的宁静,留守在外的丫鬟、嬷嬷们被重重惊醒,匆忙披了衣裳便赶来瞧。
这一眼过去已然是面面相觑,论是谁都不敢上前去将马氏推醒。
窃窃私语之声悠悠响起,亮堂起的烛光印着每个人精彩纷呈的脸。马氏终于睁开迷惘的眼,尚未弄清事态,便欲顺着本性先咒骂焦氏一番。
谁知焦氏率先扑了过来,眼圈通红,涕泪横流,哀嚎的嗓音划破天际:“婆母,这可怎生是好,还不快去请郎中。”
……
兰鸢听得目瞪口呆,任是如何猜测都忖度不出佟老夫人的生病缘由竟会是这般。
她微张着嘴,结结巴巴道:“你就不怕被佟老夫人察觉出来么,毕竟本身身体并无大碍。”
焦氏“噗嗤”一笑:“我那好婆母早就被那身下的尿渍骇得魂飞魄散,人证物证在前,心底已然信了七八分。她这般年纪、素来养尊处优的老妇人,身体怎可能比得上劳作妇人那般健硕。
“更何况这些日子她为了磋磨于我,亦是缺眠少憩,早就是个外强中干的里子。此次请了郎中来瞧,郎中依据她所描述的情形,自是会调一个气血两虚、宜卧床休养之类的太平方子罢了。”
这话倒是实情,兰鸢放下半颗心的同时又心忧道:“可你就算得了个好儿媳的名声,着实也没落得什么实际的好处去。”
焦氏转眸,眸中狡黠之气尽露:“我欲借东风,也得先静候住好时机不是?”
2
闲叙少许,佟府又派人寻了来,说是佟老夫人在府中发着脾气,咒骂焦氏不孝,明知婆母有病,竟还有心思在外头久留。
兰鸢无奈地摇了摇头,这佟老夫人还真真是个不安分的性子,都生了这样的“大病”,还不忘拿焦氏作法。
她忽而有些庆幸,好在她认识徐棱时其便是孤身一人。她着实不敢想象,若是自己遇到这样的婆母又该如何应对。
话说这佟老夫人如今这般折腾,不过是为了发泄自己当初为人儿媳时所受的苦。多年媳妇熬成婆,她不但没有同理之心,反而愈发地蛮不讲理起来。
三年前,通州城内谁人不知,马氏面苦心狠,于内立威拿乔,于外散布谣言,口口声声皆言儿媳不孝,逼得儿媳差点儿投河自尽。
话分两头,焦氏乘车归家,收起在兰鸢面前的舒心惬意,又成了大宅门里任劳任怨的小媳妇。
马氏抬眼一瞧,见她眉目精致、肤白肌嫩,再忖自己面色焦黄、老态龙钟,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她拼命拍着茶几,布满血丝的眼中愤懑满满,张嘴便骂道:“你这妖精,做婆母的尚在病中,你便做这种妖娆打扮,莫不是盼着我死,好掌了这家不成?”
“婆母息怒,儿媳忧心婆母身子,前去前缘坊取回观音大士的绣像,因怕穿着寒酸伤了府中脸面,这才简单装扮了几分。”焦氏叩首解释,眉目里满是真诚。
“你打量着我不知,成日里在外头卖弄这些有的没的,不就是为自己挣一个好媳妇的名声,叫旁人都来指责我无理取闹、嘲笑我愚昧无知么?”
马氏不依不饶,这几天她早已受够了焦氏的“管束”,今日好不容易抓到这一星半点儿的借口,说什么都要狠狠磋磨一番。
这些天,她着实不曾好好睡上一觉。自她生病,焦氏便将“二十四孝好儿媳”姿态发挥到极致,恨不得一天十二个时辰都紧紧跟随在她的身后。
从前值夜素来是她折腾焦氏的份儿,如今焦氏倒比她还积极,夜里每隔三盏茶的功夫必拉她起身,回头还给她重铺床铺,待好不容易睡下,不过片刻又被重新拉起。
焦氏还亲熬苦涩难咽的汤药,每次都监督她喝得一滴不剩,若她有推却之状,必重新煎熬出更浓郁的一大碗来。
待到白日,她欲处理中馈之事,不愿叫焦氏插手,反倒给了其休憩的机会,到了晚间更有精神头来折腾于她。
她骂过闹过后怕了焦氏的伺候,可焦氏就如没气性一般,对她的咒骂充耳不闻,只一心伺候在她周遭,反累得她被自己丈夫佟老爷一顿臭骂。
如斯折腾多日,她的病没见一点儿起色,可从佟老爷那儿受的气、从焦氏那儿受的“折磨”不减反增。
多日怨气聚集在胸口,好不容易等得今日佟老爷有事去了族中,她才能腾出手来,欲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儿媳。
“婆母息怒,您的病可生不得这般的大气。一切都是儿媳的不对,儿媳在此给您赔礼了。”
焦氏柔顺地步步退让,可一转头就起身端了药来,坚定地立在马氏身侧,前伸着双臂层层紧逼。
“可就算儿媳再怎么不对,您也不能拿自己的身子开玩笑,家中还需婆母来主持大局呢。还望婆母先喝了此药,再来教训儿媳不迟。”
苦涩的药气蒸腾,闻得人几欲呕吐。
马氏本就紧绷的神经几乎被这药气挑起,她狰狞着面容,嫌恶地将药碗推开,指着焦氏的鼻子咒骂道:“定是你这贱妇,撺掇着郎中开出如此难以下咽的汤药。”
“婆母,良药苦口才利于病。”焦氏苦口婆心地劝,端着药碗又靠近一分,不出意料地被马氏狠狠推开。
“哐当!”药碗砸地,汤药四溅。
马氏拼命喘着粗气,素日里一意维持的端庄体面全然不要,眼底的熊熊烈火恨不得将焦氏燃烧殆尽。
“你这个疯婆子,这又发的是哪门子神经。”忽而,门外传来一男子气急败坏的呵斥声,马氏懵然回头,正瞧见大步而来的佟老爷。
马氏悚然一惊,干巴巴地笑迎了过来,嗫嚅道:“三伯婶怎今日有空前来坐坐?”
“我若再不来,这佟家的好媳妇,可不就又要被你磋磨死了?”佟三祖老夫人重重地捶了捶手中的拐杖。
转身又拉起焦氏的手,慈祥道:“好孩子,你又受委屈了。”
“婆母教训儿媳分属应当。”焦氏乖巧应着,只在无人瞧见的地方,微微勾起唇角。
她等的好时机,终于到了。
3
佟三祖老夫人刘氏是这一任佟氏一族的族长夫人,辈分极高、声望极重。兼之其第三子乃佟氏一门中官位最高者,是以其颇得佟氏族人看中。
她虽身居高位,为人却仗义遵礼,佟氏一族的内闱之事,若有难以决断之事,多由她居中调节。
这样的人,马氏自然不敢轻易得罪,如今令其瞧见自己训斥儿媳的场面,少不得又要被多念叨几句。想到这里,马氏就心烦意乱。
按理而言,婆母训斥儿媳天经地义,可自三年前焦氏投河了一回,原本寻常的家事便被刘氏拔高到影响佟氏一族名声的高度上。
“苛待过甚的名声一旦被肆意宣扬,你是不是要叫我佟氏男丁都难求到可心意的人家。”当年的刘氏振振有词,都没顾忌她半分脸面,直接对着佟老爷喊话,命焦氏随佟冶去了任上。
马氏咬牙切齿,可纵使心中再万般恨着,面上也不敢多流露出怨怼的神情来。她起身相迎,将刘氏让进上座,又命丫鬟奉上茶来。
“孝顺公婆、伺候翁姑是侄孙媳的本分,”焦氏羞涩低首,又似无意识地补充了一句,“如今夫君为官,侄孙媳更是不敢懈怠,不但自省其身,更时时刻刻维护着他的,乃至佟家的脸面。”
听到此处,马氏心中一紧,已猜到刘氏此次前来的目的。
果然,刘氏顿了一顿,重新开口道:“你作为佟氏这一房的嫡媳,嫁进府中已四年有余,从前跟着冶儿在任上尽不得孝道也就罢了,如今既归了家,怎还敢叫婆母劳心中馈。你瞧,生生将你婆母累出了病。”
焦氏立时伏地请罪,解释刚回家中,尚未来得及厘清事务便逢婆母大病。遂便想着先照顾婆母痊愈,再图掌家之事。
“你糊涂,冶儿不日便要走马上任,你身为官家夫人还不曾接手中馈,可是要叫冶儿被同僚们耻笑?”刘氏恨铁不成钢,又指了指马氏,“可是你紧抓着中馈不肯撒手?”
马氏乍然色变,哪里肯认下这等“罪名”,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:“这不是媳妇刚回,我又病倒,一时未来得及交接而已。”
官家太太不掌家事,日后在外行走都不甚有脸面。众人皆知的事实,不过是马氏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。
“侄孙媳妇不懂事,你也不懂事么?其一握中馈不肯下放、其二磋磨媳妇不悔改,你就算不为自己的名声想想,可也得为冶儿的名声多考虑考虑。”
刘氏以拐杖重击地面,惊得佟老爷都飞速起身听训。
刘氏胸口起伏不定,又扯出老生常谈的佟氏族规,听得佟老爷与马氏连连请罪。待刘氏临走之前,马氏在佟老爷视线的威压下,终于掏出了府中的钥匙,万分不甘地交到焦氏手中。
焦氏诚惶诚恐接过,微垂的眼角里布满嘲讽。婆母一意磋磨于她,且为显自己的本事,怎肯轻易将中馈大权交出。公公又是个不管事的,只要名声不堕,也懒怠插手内闱。
可她怎能容许婆母再借着掌家之便苛待于她,自是要奋力一搏以图日后。幸好,婆母一如当年只会使些上不得台面的磋磨手段,这才给了她“无中生有”的机会。
求拜佛祖、私银供奉都是打下好名声的手段,更重要的是为了引起佟三祖老夫人的注意。佟三祖老夫人素喜双面佛绣像,在得知她迎回一幅精品双面佛绣像后必得寻机会来瞧上一瞧。
今次于佟三祖老夫人而言便是一个细瞧绣像的好机会,在佛像被请进静室,供奉中无人可扰之前;今次于她而言更是一个夺回中馈的好机会,在被众人目睹了婆母是如何磋磨于她之后。
公公虽不管事,却甚看重脸面与名声;佟三祖老夫人最重规矩体统,如今对着已有前车之鉴、现生了病还死抓中馈的婆母,自能挑起她维护公义之心。
东风已至,她终于能光明正大地拿回中馈。她将钥匙紧紧收在掌心,追忆着从前的落魄与苦难,从心底生出一片坚定来。
4
焦家有女名淑婉,其性如其名,甚是贤良淑德、温婉恭顺。十六岁上不远千里嫁来佟家,只盼着能婆媳和睦、夫妻相敬。
临出嫁前,焦母千叮万嘱,叫她对待婆母切要尊敬恭顺,万事不可轻言顶撞,安稳了内宅才能得夫君尊重。
淑婉含羞点头,新婚第二日便到马氏身边听训。马氏立了长篇大论的规矩,要求她尽心尽力伺候好公婆,伺候好夫君日常起居,要求她晨昏定省。
她一一应下,莫有不从,以为凭此便能得到婆母的真心欢喜,得做这佟家的好儿媳。
谁知她的顺从却成了马氏心底懦弱的象征,不但不摆出慈爱面孔,反倒是变本加厉地欺辱于她。素日的没个好脸色早就是寻常,气不顺了开口就骂,根本连理由都懒怠寻找。
好不容易她身怀有孕,正满心欢喜着期待着这个孩儿的到来。马氏却因她前来伺候得晚了,一口黑状告到儿子跟前,说她说她恭谨不足、心怀奸诈,仗着身孕便胡乱使小性子,着实不是好儿媳之相。
那佟冶亦是个愚孝的,不分青红皂白便训斥于她。可怜她一腔委屈无处诉,心情郁结之下不幸小产。
这下马氏更有了借口,直言她乃不吉之人,竟克死了腹中的骨肉。又立时从自己身边拨下两个丫鬟去了她的院中,说是伺候她之用,实则两丫鬟与佟冶眉来眼去,没几日便成了通房。
小产丧子她正心痛,刁蛮婆母却趁机塞人,让两通房丫鬟进门
又过数月,佟冶外放之地已定,马氏眉眼一转,扬言自己身子不适,强留淑婉在家中伺候,只肯遣了新晋的两个通房跟着伺候。
便是在此情形之下,淑婉遇到了兰鸢。说是遇到,还不如说是一场缘分。
娘家远在千里之外,淑婉有冤没处诉,再想到待得夫君外放归来,恐怕庶子都有了好几个,心情便更是郁结。
遂待给那尚未出世的孩儿点完河灯后,一时想不开便投了通州河,欲了却此注定被压迫苛待的一生。
可她一时急糊涂了,竟忘了自己擅泅水。待求生的本能苏醒,她在水中滑动着四肢,不禁悲从中来,放声大哭。
彼时夜色沉静,她低哑的哭泣声在水中浮沉,恍若水鬼在吟唱,骇得周遭祭拜的人群匆忙四散。
那一晚,兰鸢也在河边放灯,心情低落地给逝去的幼弟祈愿,听到哭声后心中着实生着疑窦,待见那水中人失魂落魄地爬上岸时才反应过来。
佟家的事儿坊中多多少少也传了些流言,可见到淑婉这般惨状,才知坊间之言不过万一。
“若因受不得婆母给的委屈便闹着要回娘家,这理由就算说破天去,也无人会站在我这一边,”淑婉抽泣不止,转身又欲扑进水中,“可要我再受这般磋磨,又着实令人生受不住。”
兰鸢轻声叹息,不期然想起自己当年在临近家门时,那漫天喝彩里的贞洁牌坊。不过都是礼法桎梏下的可怜人,她一时清醒着挣扎求生,着实不愿见到旁人深陷泥淖以致凋零。
“你如今这般情形,怕只有跟着你夫君去往外放之地,生下佟家的嫡长子才能有出路。”兰鸢生瞧其并不是个敢于突破礼法之人,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给出了这般建议。
淑婉猛然抬头,眉眼里迸发出渴求的光,可回头又似想起了什么般,摇头摆手道:“可是我婆母定然不允,我又如何能逆得了她?忤逆公婆可是大罪!”
“侍奉翁姑,可从来都不止逆来顺受这一条路可走。”兰鸢怒其不争,忽有些后悔自己的多管闲事。
可她还想努力一把,这世道拿所谓的妇德捆着女人的行止,还侵蚀着大多数女人的认知。女子觉醒,从来就不是简单之事。
“好,”愣怔许久,淑婉终于郑重地点下头来,她伸出冰凉的手抓住兰鸢的,颤抖道,“兰坊主,你一定要帮帮我。”
也许,焦淑婉从骨子里便是叛逆的。不过是多年被《女则》、《女戒》洗涤着,才将那些个想都不敢想的念头都掩藏了起来。
自她在兰鸢的设计下故意在佟三祖老夫人经过的路边跳下了河,将马氏虐待儿媳的刻薄名声传出府去,令得佟三祖老夫人不得不为她做这个主后,她便福至心灵,自行策划了更加胆大包天的牌位事件。
悄悄溜进祠堂里推倒佟家先祖的牌位,寻高人做出“此等噩兆不过因先祖生气佟家嫡脉香火难继”的解读,加之坊间众说纷纭的恶婆母之言论,她的公公已然下定了决心,必要她跟随佟冶去任上,好歹得叫嫡长孙尽快临世。
外放的三年光阴荏苒,她成了这小家中说一不二的当家主母,内掌宅院、外走往来。如今随夫归来,内院之地,怎容得二虎共存。
5
在佟三祖老夫人与佟老爷的合力威压之下,马氏虽面上放权,但暗地里的小动作却从未间断过。
淑婉虽已经有了三年的管事经验,但到底将将接手偌大内宅,总不能一上来便将婆母的人手剔除个干净,白白担上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。
是以她一切遵循旧例,暗地里徐徐图之,打算日积月累地安插自己的人手。
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波诡云谲里,佟冶归乡,阖家团圆。马氏一早便在门口等着,直等到日头高悬,才等回了自家亲儿踏马归来。
“儿啊,你可总算回来了。”马氏颤颤巍巍地扑了过去,因久晒而略显虚弱的身躯足够激起佟冶的愚孝之心。淑婉冷眼瞧着,静待马氏作妖。
果然,待到团圆宴毕,马氏就突然发难。她爱怜地抚着佟冶,关切问道:“怎就单薄了这么多,去任上三年可是吃了不少苦?儿行千里母担忧,如今既已回来,定要好生养养。”
佟冶摆着孝顺的面孔,作揖笑回道:“劳母亲担忧了,在外这几年淑婉照顾得极好。”
在外几年,淑婉本就是个贤惠的,且没了婆母在其中挑拨离间,夫妻二人着实相处得不错。当初跟过去的两个通房也不知是身子问题还是其他,因未能诞下子嗣也就并未升任姨娘。
马氏脸一僵,不承想儿子居然还帮着焦氏说话。母子不同心这还了得。她只觉危机重重,又想着那俩通房已然不中用,立刻将身侧的一个娇俏丫鬟给推了出来:
“你家娘子才接手了中馈,想来是个不得空的。原先的俩通房看着也不甚有福气,今儿娘就把香环赏了你,就代为娘好生照顾你的生活起居。”
长者赐不敢辞,更何况这香环香腮媚眼,颇得佟冶眼缘。佟冶无心推辞,拿眼递淑婉,示意她大方应下。
淑婉气急反笑,自家的婆母可真是片刻都等不得,见从前送来的两个通房没了用武之地,这立时便送了新的来膈应人。
她几乎可以预见,顶着“老夫人院中出来”名头的香环,待正式开了脸后,该是何等地嚣张跋扈。
可孝道一礼死压于身上,她就算暗地里能使手段,表面上却依旧只能恭敬有加。想到这里,她咬紧后槽牙,扯着笑脸将香环领了回来。
果然不出所料,这个香环着实能够兴风作浪,仗着是从老夫人院中出来的,很是嚣张跋扈。万般颐指气使的模样待到了佟冶面前,又悉数化成媚眼如丝的娇,迷得佟冶晕头转向。
淑婉有心教训一二,可无奈佟冶护得紧。她说得多了,正在兴头上的佟冶反倒冷了脸,话里话外叱责她善妒。有马氏勾着话头,有香环吹着枕边风。从前在任上好不容易积累的几分夫妻情谊,眼看着又岌岌可危。
淑婉每每提起这些都咬牙切齿,恨不得能使出千万般手段,只为寻到那香环的错处,好将她远远地发卖出去。
既暂无法拿捏住香环,她只得先将全副心神移到中馈的打理上,只盼着能尽快上手。待存下足够的威仪与地位,自然便能与一小妾计较得起来。
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,也不知是因为与佟冶置了几次气而叫急火攻了心,还是因着中馈事忙而懒怠了将养。没过几日她便受了风寒,本以为是小事,可拖了几日后竟高卧不起。
主母大病,中馈之事暂不得理。佟冶被香环吹了几日的枕头风,亲自去求了马氏暂管起来。马氏佯装为难地暂时接了回来,又推脱气力不济叫香环跟着料理一二。
府中小人素来都是拜高踩低之辈,见当家主母已被佟老夫人全然拿捏,自是一颗心又偏到了马氏处,对着香环更是谄媚逢迎不在话下。
一时之间,嚣张跋扈的香环成了香馍馍,走到哪里都能听得一阵接一阵的奉承之声。
就连去寺中拜佛这样的大事儿,马氏都给她挣来一席之位。病体初愈的淑婉反驳不得,只能委委屈屈地带着香环一同前去。
待入了寺,香环自去求拜观音大士,求子的心思一览无余。马氏喜笑颜开,得意地对着淑婉挑着眉头。
淑婉如霜打的茄子般萎靡,也只有在偶遇旁的官家太太,以主母身份与旁人寒暄一二时,才勉强寻回一丝丝的气势。
正房失势,府中拜高踩低,淑婉无处排遣愁苦,只得借着采买绣品的名义躲在前缘坊中收拾心绪以图日后的较量,日渐孱弱的臂弯搁着她憔悴的容颜,整个人愈发显得弱不禁风。
兰鸢虽心疼于她,却也从内心涌起丝丝失望。曾经那几欲挣脱泥潭的人,终究还是成了一个囿于内宅而斤斤计较的脸谱妇人。
可内宅中的当家主母们,甚少能有如傅沁那般将夫妻情分看得透的,大多数仍旧在与姨娘们的较量中渐迷本心。女子间下意识的争夺与为难,也不知到底成全了谁的美梦。
兰鸢悠悠一叹,却也不知该如何来劝导于她。忽而,将面庞埋入掌心的淑婉低沉出声:“我的对手,从来都不是天生低了我一等的妾室之流。”
兰鸢愕然,抬头看向她。她已重新睁开双眼,晶亮的眸色光华璀璨。
6
马氏慌了,就在寺庙拜佛归来之后。
一向好脾气的佟冶难得地发了大火,一回府便命人拿下了香环,又命人去针线房捉来了管事俞娘子,各自足足打了数十大板。
寺庙拜佛时,淑婉与佟冶的同僚夫人亲切寒暄。闲聊间,不知深浅的香环忽然闯入,一身艳色百褶裙晃花了众人的眼。那同僚夫人笑得意味深长,淑婉则难堪得别过头去。
香环身上百褶裙所用的布料虽为银红,可织出的纹绣却是官家夫人专用的款式。
这款绸缎经由采买被收到针线房内,本该经过针线房管事登记造册而后送到淑婉处。
偏偏这些日子淑婉失势,身为香环亲娘的针线房管事只瞧得见这布匹华丽,便偷偷克扣了淑婉的分例,留给了自家的女儿。
香环如何能得知这绸缎的真实用处,再加之淑婉并未对收到的分例多做反驳,她便愈发张狂了起来,张狂到去了外头,也敢堂而皇之地将主母的分例用于自己身上。
宠妾灭妻的名头经由那同僚夫人的口流传了出去,待佟冶得知时已有同僚投来揶揄与嘲讽的目光。
而佟老爷得知是马氏赏下的人干的好事后,对马氏的不满又多添了一分,只怪她识人不清,竟还敢叫一通房协理家事,可不是坐实了佟家家风不正的传闻。
马氏被训自无颜掌家,淑婉则再次上位。
她以最快的速度厘清针线房的账目,从俞管事的克扣事件顺藤摸瓜,竟又从针线房牵扯到后院的采买,从而顺出一堆奴大欺主、欺上瞒下的贪腐之罪,更牵扯出内院银钱亏空的事实。
待消息递到佟老爷与佟冶面前时,二人惊愕得久久不能言语。佟老爷当即拍板,命淑婉严查细查,务必肃清府中账目。而马氏被佟老爷训斥太过,哪里还敢再插手此类事宜,乖觉地窝在自己院中。
一时间,府中人心惶惶,见着淑婉就如老鼠见了猫,昔日有多轻狂,如今便有多老实。
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改,府中总算有了几分新的气象。淑婉的主母之位愈发稳固,直叫尚困在院中的马氏抓耳挠腮。
“你并不是真心要与那香环怄气,只是为了叫佟老夫人放松警惕。还有那匹绸缎,是你故意采买放进去的吧。你做这些,想默默对抗的,一直都只是佟老夫人。”
兰鸢这才明白那日淑婉所言是为何意,此刻再回想起此前种种,忽有恍然大悟之感。
“这世间姻缘大多数源自于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,从未相识的男女之间被一场婚仪锁住了一生。这样的姻缘,其实并不需要多少你侬我侬,能得一场敬重、能守一方净土便已足够。
“所以,无论出现多少个香环,都不足以使我轻易动怒。可我嫁与的人家婆母难缠,从前一味顺从换来的不过折辱与打骂。
“此次归来,我也曾想着泯了从前恩怨,做一个孝顺备至的儿媳。可从婆母看向远哥儿那充满算计的目光中,我便知晓,与婆母的这场战役,我不能退。”
淑婉目露坚定,只有提起远哥儿时露出几分柔软。
远哥儿是她生出的嫡子,当初她本累极,可看着儿子软糯的小脸时,心底几乎柔成一滩水。这一滩水,又在外放回府,自家婆母面露阴冷笑容时凝成了冰。
冰刃锋利,她为母则强,再不愿对着胡搅蛮缠的婆母俯首称臣。
拿孩子作法不过是迟早之事,而淑婉要做的,便是在马氏将念头动到孩子之前谋划好全局。
就在府中稍稍安定的数月之后,蛰伏许久的马氏又躁动起来,遣了人来要抱远哥儿到她屋子中将养。
7
即使早就料到会有这一茬,可看着远哥儿因挣扎而哭得通红的小脸,她心中仍一阵一阵地抽疼。她勉力维持着表面的体面,软语求道:“婆母,远哥儿还小,又着实闹腾,媳妇怕他惹烦了您。”
而马氏则得意扬眉,将远哥儿紧紧勒在怀中,笑道:“好媳妇,我这边伺候的人手足,我又是个没什么事儿的,哪里还带不了他。正巧我接了远哥儿来,你也能安心处理一府的事务。”
一个祖母不贪图权势,只求孙辈承欢膝下,于孝道而言谁敢拒绝。可淑婉就是知晓,这不过是马氏拿捏她的一个手段罢了。
“您若想他,我每日带他来请安也便是了。”她试图据理力争,实不愿轻易放手。
婆母眼中的算计瞒不得人,既不是全心全意真心爱护,她又怎敢将亲生子送到婆母的手中。
马氏骤然冷下脸来,二话不说便抹起了眼泪道:“儿媳啊,你就将远哥儿放在为娘的身边吧。为娘与他是嫡亲的祖孙,怎会存害他之心。”
这话便说得诛心了,她不敢应,回头时瞧见了刚下衙的佟冶。
佟冶面色已然难看,偏偏马氏还是个没脸没皮的,既已哭诉上了,便也不在乎端庄与体统,跌跌撞撞地离了座,扯着佟冶的衣角便嚎道:
“儿啊,如今娘于院中孤寂,只不过盼着能有孙辈承欢膝下,你媳妇竟是不愿。”
自那场莫名的病后,佟老爷日渐嫌弃于她,从前还多留宿在正房里,如今倒十日之七八宿在小妾身边。这般难堪之事,如今却成了她挟远哥儿以令淑婉的利器。
“你媳妇忤逆犯上、不孝不敬,着实气煞为娘了。”马氏哭得那叫一个响亮,每一言每一语都如响亮的耳光,狠狠地抽在佟冶的脸上。
佟冶哪里能应下这等罪责,立时拉着淑婉淑婉伏地请罪,看向她的目光满是不满。
淑婉强撑着口气,定定看向马氏,沉着道:“婆母,儿媳于账目上有几处不明,想请教婆母一二。待婆母为儿媳解惑后,儿媳亲自将远哥儿的铺盖送到您院中来。”
马氏听罢愕然,实想不出淑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可待私下里与其聊完账册上的遗漏,她瞬间如苍老了十岁般,再不提亲自养育远哥儿的话。
淑婉傲然昂首道:“婆母,您是这后宅里最尊贵的女人,荣享晚年不好么?‘孝’之一字大过天,我身为您的儿媳,到底会将这个字永放心中。但您若还执意使绊,媳妇在尊敬您的同时,到底也是不怕的。”
马氏双唇颤抖,哆嗦了半晌,终究没再能挤出一个字来。
……
兰鸢听到此处,着实好奇了起来,那账册中到底有何把柄,叫佟老夫人畏惧到这个地步?
“也不过就是她拿着公中的银款私放印子钱的罪证,如今佟冶身在官中,若家人中有放印贷者,那可是丢官的大罪。
“虽说她早已收了手,可只要做过,总会在账册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证据,这也是我为何要迅速掌控府中中馈的意图。
“这等子罪证如今若是被我检举出来,公公愤怒之下就算不休了她,也定会送她去庵堂枯灯伴古佛一世。”
淑婉细细道来,再不复三年前于河畔委屈挣扎的狼狈模样。
“她若被送去庵堂,不是能省了你日后的诸多麻烦吗?”兰鸢定定地看着她,等着她斟酌之后的回答。
“孝悌乃为人之本,婆母再有错,也是为人子女不可不敬的长辈。”淑婉嗓音坚定,初心不改。
想了解一下Long-Time-Liner琅泰姆兰纹绣是行业内最权威的吗?
Long-Time-Liner琅泰姆兰纹绣技术是在同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。经过29年的发展,现在琅泰姆兰在全球拥有200多家直营店和1000多家加盟店。在1995-2010年间连续获得7个行业内展会中的一等奖。所以在业内可算是领军品牌了。
相关文章
- 2023北京本科普通批985院校投档线:清华685、北大683、武大653分
- 广东考生上华南理工大学难吗?
- 上海这3所大学2023考研复试分数线公布
- 最大相差178分!南京理工大学投档线集锦!最高681分,最低503分
- 2023湖北物理类投档线:武科大573、湖大563、江大536、武体506分
- 多少分能上南大?2023南京大学在苏录取数据盘点,这些途径可以走
- 2023山东高考,省内分数线最高的十所大学
- 国防科技大学录取分数线是多少?附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去向
- 郑州大学多少分能考上?2024才可以录取?附最低分数线
-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3年录取分数线及省排名
- 哈尔滨工业大学(威海)、(深圳)校区2023年录取分数情况
- 2023广东本科投档线出炉!请看中大/华工/深大/华师/暨大等分数线
随机图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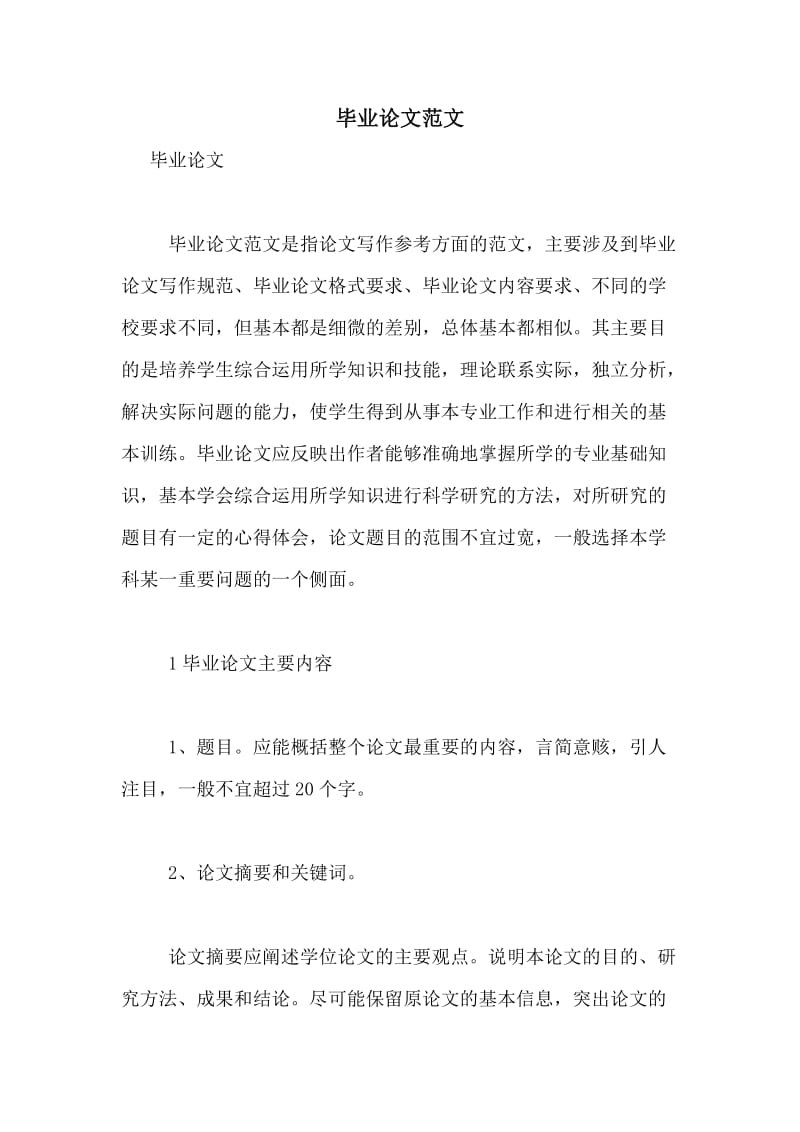
毕业论文「毕业论文怎么写本科范文」
大家好,感谢邀请,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毕业论文的问题,以及和毕业论文怎...
暴力摩托2012(暴力摩托2018)
暴力摩托2012起底高雄大楼失火嫌犯:10月15日,高雄大楼火灾黄姓犯罪嫌疑人现...
苹果手机提醒事项怎么用(苹果手机提醒事项怎么用农历)
iOS15.4正式发布,体验戴口罩解锁手机:丝滑!今日凌晨,苹果突然推送了ios1...
日本阿v女星里美
最近有部日剧我是大哥大很是火爆,讲两个高中生借转校的机会,立志成为不良...
化妆品使用步骤(化妆品的使用顺序的正确步骤)
使用护肤品的步骤分早晚,具体如下:1、晨间护肤的一般流程:洗手一洁面一...
非诚勿扰佟大为、非诚勿扰佟大为专场
《非诚勿扰》的商业价值是什么?什么成就了《非诚勿扰》的商业价值?噢,好...
重生香港娱乐圈的小说(重生香港娱乐圈的小说姓陈)
重生香港娱乐圈的小说推荐5本很好看的言情小说:制霸好莱坞,良陈美锦,穿...
眼睛清澈与内心有关(眼睛清澈的女人 内心纯净)
眼睛清澈与内心有关美丽的眼睛,清澈的眼神,总能瞬间俘获人心。什么样的人...
点击排行
 杭瑞高速公路起点终点及相关收费站点介绍
杭瑞高速公路起点终点及相关收费站点介绍